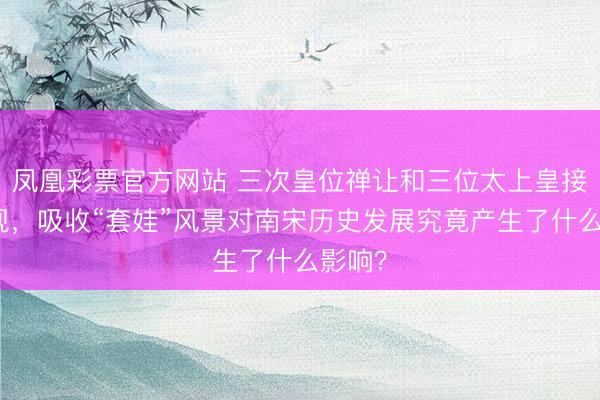
绍兴三十二年春天,临安城的雨下得很细。宫城深处,高宗赵构颁下禅位诏书,把皇位交给养子赵昚的讯息,很快就从殿阁里传到商人巷口。好多老庶民只当是“官家换了个东谈主”,却很少有东谈主思到,这一次看似安祥的禅让,会在以后一百多年里被一再借鉴、反复演出,终末险些把南宋的命根子折腾空了。
故风趣的是,这种一再“套娃”的禅让,口头上谨慎“慈父让位、贤子承统”,看起来慈祥体面,实则无间减弱皇权,把朝政主动送到了昭脱手里。比及蒙古雄师卷土南下时,南宋的皇位还是不是领会的核心,而更像一把轮番坐的“高座”,谁齐不敢信得过坐稳。
一、从靖康余波到皇位“清偿太祖”
要看南宋皇位吸收的怪圈,绕不开靖康之变。1127年春,宋徽宗、宋钦宗父子被金军掳走,北宋沦一火。赵构在江南仓促诱惑南宋时,年不外二十露面,按说还有大把的时间不错从头立家业、育子嗣。他自后之是以走上禅让之路,并把皇位“清偿”太祖一系,与个东谈主遭逢和宗室凋零,齐有平直干系。

高宗的独子赵旉短折,这是一个硬伤。更不毛的是,在金军掠夺汴京时,北宋宗室险些被“一锅端”,无数太宗系子孙或被掳、或失散,原有的宗室收集被打断。再加上高宗在战乱隐迹中的惊恐与伤病,使他失去了再育的可能,皇位吸收问题倏得变得难办而敏锐。
值得一提的是,其时坊间的说法很玄。有东谈主借“解梦”之名告诉高宗,说赵宋国运之是以遇到靖康大祸,是因为夙昔太宗夺了太祖之位,欠了天谈一笔账,不清偿,总会出乱子。这话听贪恋信,却戳中了高宗心里的软肋——毕竟,从太祖到太宗的权柄叮属,本就笼罩着“斧声烛影”的暗影,朝野齐噤而不宣,却又心知肚明。
试思一下,一个靠着“半壁山河”拼凑延续的皇朝,死后站着的是一段说不清、讲不解的“弑兄”“篡位”外传,再叠加靖康之耻的惨烈悲哀,高宗很难分辩所谓“太祖、太宗之争”有所顾虑。于是,把皇位“送回”太祖一系,既像是补一笔旧账,又像是向天地讲明:赵宋至少在口头上,还尊重“正宗”。
在这种神色和现实双重激动下,太祖第四子赵德芳的后代被从头提上台面。流程筛选,高宗选中了赵德芳八世孙赵伯琮,更名赵瑗。赵瑗被定为储君后,足足在临安宫城里等了三十多年,时间还要面对另一个竞争者赵璩。两东谈主比起门第齐差未几,信得过拉开差距的是品行和口碑,赵璩过于骄纵,植党自利的风声无间,天然落了下风。
绍兴二十九年,赵瑗被肃肃立为太子,更名赵玮。三年之后,高宗又以“禅让”口头将大位传给这位太子,并再更名为赵昚,是为宋孝宗。看口头,高宗一副“师法仁宗”“公天地”的姿态,身为太上皇仍掌捏实权,影响朝局长达二十五年。试验上,这第一次禅让,为自后的“太上皇—新帝”双重权柄结构开了头。

这种权柄结构有一个隐患:天子并不是信得过风趣上的“最高裁决者”。太上皇在、皇权分两层,宰相、重臣就不错傍边逢源,找“高的那位”或“新的这位”谈话。后世的韩侂胄、史遥远、贾似谈,恰是在访佛的漏洞里一步步坐大。
二、孝宗北伐心结与“看走眼”的太子之选
孝宗登基之初,是南宋一段稀有的精神飞腾期。1162年,他一上台就喊出“复原华夏”的标语,亲身北伐,在淮河一线与金军营救。不少史家赞他“威武类太祖”,至少阵容上,确乎和偏安阶梯拉开了距离。
不外,故风趣的是,这位立志要立功立事的天子,在治家方面却牵丝攀藤,尤其在立储问题上反复扭捏。刚登基那几年,锻练的宰相张浚就领导过他:“东谈主主新立,当早建东宫。”风趣很明白,皇位吸收要早定,免得朝堂东谈主心浮动。但孝宗心里有顾虑,一是顾虑过早立太子刺激太上皇高宗,二是把大部分元气心灵压在北伐上,对内廷问题反而提不起酷爱酷爱。
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,是他对几个女儿的评价并不一致。宗子赵愭疼爱诗文,本性偏文弱,孝宗总以为“不像干大事的东谈主”;第三子赵惇则性格刚烈,被他视作“威武类己”,更得当心中理思的吸收东谈主形象。只不外,在官修史册以外,任何一个父亲的偏疼,落在皇位吸收上,齐会变成一颗隐雷。
在野臣压力下,孝宗终究照旧信服礼法,将宗子赵愭立为太子。谁也没想到,这位太子命薄。一次出行途经贡院,恰逢举子云集,清谈不利,随从与举子发生突破,地方一度繁杂。太子本就体虚,又受到惊吓,回宫后邑邑成疾,不久病逝。这一变故,不仅打乱了孝宗的蓝本安排,也把“立谁为太子”的问题从头推上台面。

这下,孝宗趁势立第三子赵惇为太子,看似严容庄容,试验上埋下了以后宫廷风云的种子。赵惇在东宫一呆十几年,看着父皇既要顾虑太上皇,又千里浸在复原业绩里,不免心生虚夸。有一趟他试探性地对孝宗说:“臣还是生白胡子了,有东谈主送药染白胡,却不敢用。”话不长,风趣很平直:年级大了,却长久在太子位上拖着。
不得不说,赵惇这句话,说到了孝宗心里的犹疑处。二十余年的北伐勉力,战果有限,他我方也嗅觉力不从心。高宗夙昔提前禅位,为他树了一个神志,他并非莫得用仿的冲动。不外,其时太上皇尚在,权柄花式并不只纯,任何一步大作为,齐得推测成果。
直到1187年,高宗物化一年之后,孝宗才终于下定决心,将皇位禅让给太子赵惇,是为光宗。禅让本来是个体面安排,但对孝宗父子干系,却是全部隐形刀口。禅让之后,孝宗仍然对朝政保持强横酷爱酷爱,尤其在立太子的问题上,再一次作念出打扰——他看中了魏王之子,以为比光宗的独子更像可塑之才。
这件事,成了父子心理的回荡点。光宗听到这个想法,“心中如遭雷击”,嘴上不敢反对,只可顺着容许。父亲志在“择贤”,女儿却只看到“废己子另立”,两东谈主的态度越来越难以斡旋。不错思象,在那之后,每一次觐见,每一句问安,齐带着暗潮。
从汗漫看,孝宗确乎“看走了眼”。他对光宗的政治判断,更偏重“威武”气质,而忽略了内心承压才略。一个经不起夹攻的东谈主,被挤在太上皇与内廷势力之间,很难不出现问题。

三、“惧内天子”与疯癫太上皇的宫廷乱局
光宗即位后,凤凰彩票官方网站宫廷的主导力量悄然发生变化。孝宗还在,照理说太上皇仍是一个压舱石,但光宗平素信得过短促的,却是皇后李氏。李皇后诞生不高,却极有手腕,而况素性妒悍。光宗早年就对她言从计纳,即位后更是步步戒备。
一个小细节不错看出李皇后的强势。孝宗夙昔册立夏皇后时,只推恩十八位娘家谱属,这是其时的成例。轮到李氏作念皇后,她坚持要推恩二十五东谈主,彰着并列致使高出太上皇后的位置。朝臣心知不当,反复折中,终末定在二十一东谈主。看似数字上的折中,背后却说未来子还是被牵着鼻子走。
在立太子问题上,李皇后天然但愿我方的女儿嘉王赵扩得以入主东宫。孝宗偏疼魏王之子,李皇后不仅抵抗,还迎面顶嘴。一次宴席上,她当着孝宗的面拿起此事,要求册立嘉王为太子。孝宗不允,她马上发作:“我是官家的合髻爱妻,我亲生女儿为何不可立太子?”饮宴不欢而散,后宫矛盾肃肃撕开。
他说父亲偏心,她说太上皇压东谈主,李皇后不竭在光宗耳边挑拨,双方的话越听越乱。一个夹在中间的天子,既枯竭定力,又枯竭派头,终究在重压下倒下。光宗自后一场大病,病好之后精神景色彰着十分,时而领悟,时而絮叨,言行活动经常出东谈主料思。

到了1194年,孝宗物化,照礼法光宗应亲临丧礼,主理大行天子的葬仪,这是再怎样心虚的君主齐不会缺席的大事。偏巧光宗拒绝亲行,躲在深宫不出。此举不可不说触碰了朝臣和士医师心中的底线,群情汹涌,对天子的质疑马上加重。
这一年,赵汝愚和韩侂胄站到了前台。他们一面强调“社稷为重”,一面寻求正当性守旧,于是把眼神投向吴太皇太后——也即是高宗皇后吴氏。其时成就新君的决议,落在光宗之子嘉王赵扩身上。废父立子,本就敏锐,何况嘉王我方也方寸已乱。
史册中有一幕对话,颇能反馈那种痛苦局面。群臣劝进时,嘉王一再陨泣,迟迟不敢接待。吴太皇太后看不下去,责问谈:“我见过你太爷爷、你爷爷仕进家,没见过像你这么的。”话不客气,却说出了宗室长者的无奈。终末,只不错“太后命”强行径他披上龙袍,是为宁宗。
有极少很值得玩味:宁宗即位时,光宗本东谈主并不知情。等他发觉我方成了被架空的太上皇,精神愈加失常,在宫中疯跑,乱七八糟。宫女内侍擅自称他为“疯天子”,不敢围聚。清代学者王夫之评他“视晋惠帝,差辨菽麦耳”,风趣是,比起阿谁连食粮齐分不清的晋惠帝,只稍强一线。
这一出禅让闹剧,从政治层面看,是一次“以废代立”的权柄重排。赵汝愚、韩侂胄借太后之名,完成了皇位的再分派,朝廷口头上有了新天子,信得过捏权者却是那些操盘的昭着。宁宗性格柔软、枯竭办法,本能地依赖这些辅政大臣,皇权进一步空腹化。

从高宗、孝宗到光宗,三代天子齐曾戴上“太上皇”的名号,但信得过捏实权的,经常不是阿谁“上”的,而是站在太上皇与新帝之间的宰相、外戚与厚交。禅让的相貌越体面,本体权斗就越灭绝。
四、宁宗、理宗、度宗:皇位“套娃”与南宋尾声
宁宗上台之初,朝局一度出现过一刹的整顿迹象。赵汝愚主政时,试图扶直皇权,压制宗室和外戚,复原一定的政治步骤。但这么的尝试莫得督察多久,权柄天平很快倾向更为激进的韩侂胄。
韩侂胄借“外戚”身份起家,又诳骗“义子”“厚交”等干系网,紧紧收拢宁宗。他我方并不雀跃于幕后掌权,还思通过对外干戈从头塑造声望。嘉定年间,他高调发动北伐,但愿重演夙昔孝宗的复原地方。缺憾的是,战事准备仓促,阵线拉得过长,终究以失败告终,韩侂胄本东谈主也在野中反对声中被正法。
这一轮折腾,削耗了南宋本就有限的国力。宁宗本东谈主在政治上越来越力不从心,最终走向了另一种“托孤阶梯”——天子无子,必须再一次从宗室里挑东谈主顶上。于是,史遥远登场。

史遥远本性严慎,善于在漏洞中寻找安全的位置。他深知天子越弱,我方越稳。宁宗无嗣之后,他绕开近支,选中了一个昌国公主府中的宗室后生赵昀,也即是自后的理宗。这位来日天子其时不外十几岁,被仓促推上皇位,一运转对朝政并无主导力。
{jz:field.toptypename/}理宗继位后,口头上朝廷换了新征象,试验上权柄重点紧紧落在史遥远手里。史氏以“保全社稷”为名,对内压制异己,对外实践偏安,不再奢谈北伐。理宗在这种氛围中长大,养成了对政治酷爱酷爱不高、对享乐不甚节制的本性,这极少在他晚年尤为彰着。
更具调侃意味的是,理宗也无子。皇位再次靠近“无嗣”的痛苦局面。既然前边还是有了高宗“择宗室为嗣”、宁宗“委用昭着立嗣”的前例,理宗这一次就更严容庄容地重叠旧路——从宗室中挑选一位侄辈入继。这位被选中的宗室子弟,即是自后被称为“度宗”的赵禥。
赵禥诞生支系,并非从小按照“来日天子”的法式培养,少年时就千里溺声色。史册对他的评价并不客气,说他“喜燕乐,不亲万机”,通俗说即是对政务不上心,对享受很在行。理宗斟酌皇位传承时,其实并不是莫得其他聘任,仅仅诸多条目衡量下来,这位侄子算是“拼凑可用”。
度宗一登基,南宋还是过问严重内忧外祸的阶段。蒙古在朔方归拢,随后与南宋之间的对峙浮松升级。朝廷里面,昭着贾似谈一度掌捏军政大权,试图通过一系列酬酢和军事本领拖延蒙古进攻节拍,却又在对外干戈中屡屡避讳实情,装潢太平。

在这么的大布景下,皇位吸收的“套娃模式”还是酿成固定旅途:天子无嗣,就选宗室;选了宗室,时终年幼或根基不及,独一把权柄再交给宰相、外戚或近臣;这些东谈主为了本身安全,会尽量让天子保持“可控”,多一层太上皇、再加一位新君,权柄就有了更多腾挪空间。
故风趣的是,从高宗到度宗,三次禅让、三个太上皇,险些每一次皇位叮属,齐伴跟着昭着崛起:高宗—孝宗之间,有张浚、秦桧的角逐;孝宗—光宗—宁宗这一线,有赵汝愚、韩侂胄轮番上台;宁宗—理宗—度宗这一线,则是史遥远、贾似谈的天地。天子越来越像被推来推去的棋子,太上皇这个名号,也失去了稳局的风趣。
从历史汗漫看,南宋的沦一火,天然有外敌坚硬、地舆局限、经济职责等综合要素,但皇位吸收历久不稳、权柄结构层层“套壳”,确乎减弱了这个政权的违背才略。储君之争、太上皇与新帝的好意思妙干系、昭着在其中的穿梭游走,一次次消费朝廷的元气,也消磨了士医师阶级对皇权的信心。
黄宗羲也曾轮廓南宋的教师,说南宋之一火,很大一部分在于“君德落寞、立储不当”。回看这几场禅让,就能感到他的判断并不夸张:每一代东谈主齐在试图处理目前的吸收问题,却很少有东谈主信得过斟酌到轨制层面的永久成果。禅让本该是柔性的权柄叮属方式,到了南宋后期,却一步步变成权柄博弈的遮羞布。
到了度宗朝,蒙古军南下的脚步还是无法阻拦,临安城外的阵势一日紧过一日。宫廷深处,天子、太上皇、昭着之间的那套纯属戏码,依然在延续。南宋这艘大船看上去还在飘动,船舱里的纰谬其实早已布满总共这个词龙骨。
